醫生接過檢查單一看,眉頭深深蹙起:“我記得這個孩子,骨髓庫有合適的骨髓源。”阮綿倏然睜大了眼,還沒來得高興,便聽醫生嘆氣道:“可惜沒有家屬,也沒有50萬的手術費,生生耽誤了。”走出就診室,阮綿的耳畔還...
窗外的雪越發大了,砸在玻璃上,震得阮綿眼睫一顫。
她的心都在淌血,卻只能擁著裴揚瘦小的身體,哽咽道:
“不會的,她一定會接你出去的。”
沒想到,裴揚竟主動開口安慰:“阿姨,你是哭了嗎?是不是哪里疼?我幫你叫院長阿姨來好不好?”
她的兒子,在她不在的三年,長成了這么善良的模樣。
“不疼,我只是……”
我只是心疼你,我的兒子。
可這話到了嘴邊,阮綿幾度張口,卻什么也說不出,反倒是眼淚流得越發洶涌,怎么都止不住。
她抱了裴揚很久很久,才依依不舍放開。
接下來的一個月,阮綿拼了命地工作兼職,每天睡眠時間不超過三個小時,每每夜里都是噩夢。
醫生冷冰冰拒絕:“對不起,你的錢不夠,我們不能給他安排手術。”
裴揚拉著阮綿的袖子:“媽媽,我好疼……”
絕望的盡頭,是裴盡冷若冰霜的臉。
“你休想湊夠150萬接他出來,野種,就不配活在這個世上。”
“不!”
從睡夢驚醒,阮綿額上都是冷汗。
她像是一條脫水的魚,拼命呼吸,肺里卻是空的。
寒冬的冷意撲面而來,鉆入骨髓。
阮綿翻出手機,視線落在手機里的銀行卡余額短信上。
做手術還差20萬,接揚揚出福利院,還差120萬。
明明從監獄出來,她就知道自己已經不是富家千金,只是一條又窮又賤的狗,洗碗、掃大街、能做的都做了。
可上天和她開了個巨大的玩笑,她絞盡腦汁想盡辦法,還是沒法湊齊50萬。
手機上的日期又多了一日,仿若死亡倒計時。
阮綿胸膛劇烈起伏,盯著撥號界面凝了許久,才撥出那個滾瓜爛熟的號碼。
裴盡的聲音沒有絲毫波瀾:“什么事?”
阮綿一頓,聲音放得很低很卑微。
“裴律,我求您了,我不要120萬,只要20萬,求您讓揚揚活下來。”
“你一個沒人要的殺人犯,拿什么求我?”
她白著唇,幾次張口才發出聲音:“我……我的身體。”
裴盡眉頭微微蹙起,眸子晦暗不明。
“來洲際酒店304。”
說完,不等阮綿回答便掛了電話。
好似她只是一個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玩物。
阮綿不敢怠慢,匆匆趕往洲際酒店。
冬末雪花飛揚,打在阮綿的臉上,刺骨的冷。
酒店的暖氣一吹,身體沒有絲毫熱意,只剩冷熱交替的煎熬。
裴盡坐在沙發上,金絲眼鏡閃著清冷的光,上下打量著阮綿。
“你就這么過來的?”
阮綿下意識垂眸看去,才發現自己出門太過著急,只在睡衣外披了件外套,路上一跑,領口已然敞開大半。
若是從前,她早就羞恥得無法見人,可此時此刻,就算是天塌下來了也沒有自己的兒子重要。
更何況,尊嚴這種奢侈的東西,從她入獄第一天起,她就不再奢望。
裴盡要她過來,不就是要她的身子嗎?
阮綿極力壓下心中的恥辱,一步步走到裴盡面前,閉上眼吻上他的唇。
沒有記憶中的溫柔,只嘗到一片苦澀。
感受到阮綿的眼淚,裴盡心中忽然一抽,猛地推開阮綿。
“別碰我,我嫌臟。”
最后一絲自尊被這句話碾滅,連呼吸都格外吃力。
裴盡抽出一張銀行卡扔在地上。
“20萬,買你離開京市,永遠不準出現在我和安安面前。”
這話宛若一把利劍,直直刺進阮綿的胸口,鮮血淋漓。
他連她最后一點念想,都不愿留給她嗎?
可想到裴揚一點點瘦弱下去的身軀,阮綿五臟六腑都絞碎了。
她彎下腰撿起銀行卡,用盡全身的力氣才說出口:“我發誓,手術之后就離開京市,永遠不回來,不會出現在你和溫安安面前。”
 時岑冉秦川野 分類:都市
作者:神秘人 主角:時岑冉秦川野
時岑冉秦川野 分類:都市
作者:神秘人 主角:時岑冉秦川野
 他們已再無緣相見 分類:現情
作者:俠名 主角:季暖沈聞川
他們已再無緣相見 分類:現情
作者:俠名 主角:季暖沈聞川
 林芝瑤傅淮生 分類:現情
作者:小說家 主角:林芝瑤傅淮生
林芝瑤傅淮生 分類:現情
作者:小說家 主角:林芝瑤傅淮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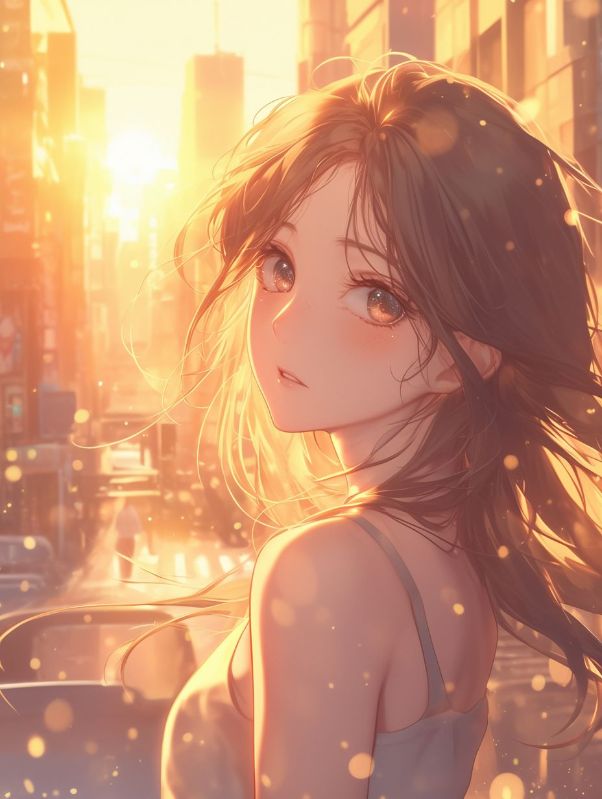 老板娘強迫我喝咖啡,在大廠暑假實習的我殺瘋了 分類:都市
作者:天璣 主角:姜念云張新海
老板娘強迫我喝咖啡,在大廠暑假實習的我殺瘋了 分類:都市
作者:天璣 主角:姜念云張新海
 女兒四歲生日這天,老公帶五歲私生子回家了 分類:現情
作者:啵啵珠 主角:許澤遠許詩意
女兒四歲生日這天,老公帶五歲私生子回家了 分類:現情
作者:啵啵珠 主角:許澤遠許詩意